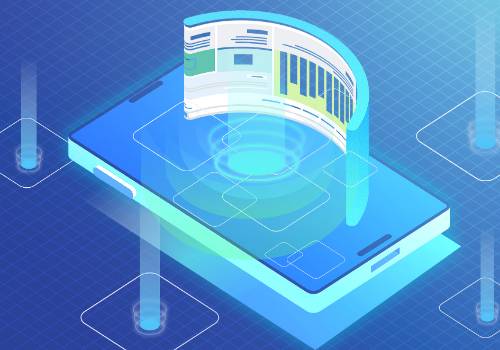撰文|蔡磊
摘編|周琪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對 45 歲的蔡磊來說,人生分為兩段。41 歲之前,他事業有成,建立家庭,初為人父。他曾長期擔任京東集團副總裁,是中國電子發票的推動者。而在 41 歲這一年,他收到了一紙“漸凍癥”的確診通知書。
“漸凍癥”是一種罕見病,全球患病率為 5.2/10 萬,平均生存期 2-5 年。數年來,科學家們一直試圖找出這個罕見病的發病原因以及治療方法,但進展有限。對患者而言,它比癌癥更可怕。得了這個病,只能緩慢而不可逆地一步步走向讓人失去尊嚴的死亡。
如果你長期關心蔡磊,會注意到他的身體狀態正在肉眼可見地變差。2022 年是他病情進展最顯著的一年,年初左臂無法平舉,年中發現右臂也抬不起來了,手指也一根根倒下,失去了力量,只能用腳踩裝置來操作鼠標。更難的是,伴隨喉部肌肉的萎縮,說話開始費勁了,發音慢慢含糊,以前講一遍就能語音識別,現在總要講好幾遍。吃東西時,普通大小的湯圓變得難以下咽。
但他依舊在和時間賽跑,推進“漸凍癥”患者遺體和組織樣本捐贈,搭建最大的“漸凍癥”病理科研樣本庫,設立公益基金與慈善信托,對早期科研給予持續資助,推動多條“漸凍癥”藥物管線的建立,開啟直播對“破冰”事業持續支持……用他自己的話說,打光最后一顆子彈。
相信蔡磊的故事與精神會打動每一個努力生活的人。在沉重的疾病與命運前,在面臨幾乎不可能之時,縱使不敵,也絕不屈服。以下內容摘自蔡磊所著《相信》,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人生倒計時
從住院第一天起,我就開始了解漸凍癥的相關知識。起初是通過網絡搜索看一些官網,后來開始查專業文獻,把國內外學術期刊網上所有可以找到的關于運動神經元病,包括關于神經退行性疾病的論文,全部下載下來,逐字逐句地讀。為了提高讀論文的速度,我還找到了專業的醫學翻譯軟件。夫人是藥學出身,她一看,軟件翻譯得很準確。經她驗證后,我便開始海量地翻譯、閱讀,翻譯、閱讀。
讀得越多,越了解這個病,我也越能體會到樊醫生(北醫三院神經內科主任樊東升教授)說的這個病的殘酷之處。
神經退行性疾病一般是指由神經元逐步凋亡或功能受損導致的疾病。像帕金森病、阿爾茨海默病,都是重大的神經退行性疾病,只是作用于不同區域的神經元細胞。當中腦的多巴胺能神經元受損或凋亡,經常會導致帕金森病;當顳葉內側海馬神經元細胞死亡,人的記憶會退化,一般表現為阿爾茨海默病;而當運動神經元出現問題,則會導致運動神經元病(最典型的是肌萎縮側索硬化,俗稱“漸凍癥”)。
人體的骨骼肌是由運動神經元支配的,當神經元凋亡,肌肉失去了支配,就會逐漸萎縮,以及出現腱反射亢進、肌張力增高、肌束顫動等癥狀。
“肌肉逐漸萎縮” 6 個字背后,是常人難以想象的折磨和痛苦。喝水、吃飯、穿衣、上廁所、拿手機、打字、發聲……你會眼睜睜看著這些曾經輕而易舉的事情變得難如登天,甚至你都沒法自己翻身。疾病發展到后期,人的身體會像“融化的蠟燭”一樣坍塌下去,無法說話,也無法吞咽,“吃飯”要靠胃管往胃里注入食物,呼吸需要靠機器維持,大小便無法自理,排便的時候需要人工去摳。人會活得毫無尊嚴可言。
其實“漸凍癥”專指肌萎縮側索硬化,后來民間將其含義逐漸擴展了,也用來描述有類似癥狀的其他疾病,不過這樣是不確的。雖然媒體上時不時會出現“某某漸凍癥患者被治好”的消息,但嚴格來說,目前能治好的都不是肌萎縮側索硬化。肌萎縮側索硬化患者的平均生存期僅有 2~5 年,就算有人一天 24 小時寸步不離地看護,鮮少有人能活過 10 年。
世界上最極端的例子是霍金,這位全球最著名的漸凍癥患者, 21 歲確診后,醫生判斷他只能活兩年,但他頑強度過了 55 年, 76 歲去世。之所以能創造這樣的奇跡,一方面得益于他本人樂觀向上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是最為關鍵的,就是漸凍癥的分型不同,這也是影響患者生存期的決定性因素。近年研究主要將漸凍癥分為數個臨床表型,霍金的病型有可能屬于一種可以避免呼吸系統受損的疾病類型。幾乎大部分漸凍人最后都是因為呼吸衰竭而死亡,所以如果呼吸系統不受損,患者通常存活率較高。
當然,霍金的奇跡也有賴于頂尖醫護人員數十年如一日的細致護理。他日常的進食主要依靠護理人員,避免了可能因吞咽肌肉退化導致的脫水或營養不良。對于他,可謂傾國家之力去維持他的生命,最先進的醫療設施、最專業的護理團隊,成本高昂到一般人無法想象。
所以,他的案例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例,是所有漸凍人都無法企及的幸運。
對普通患者來說,就算有人全程照顧,想維持住他們的生命也并不容易。漸凍癥患者的死因各種各樣,有呼吸受阻、被一口痰堵住導致死亡的,有呼吸機突然斷電而死亡的,有絕食、自殺的,也有被家人放棄而死亡的。
還有一種情況——走路摔死的,這個死因聽起來簡直匪夷所思。普通人走路摔跤的時候,會本能地用手撐地,保護頭部,而上肢發病的漸凍癥患者,兩只胳膊喪失了支撐的力量,只能眼睜睜地讓自己的頭砸到地面,有時候就這樣直接摔死了,即使沒摔死,也要縫上十幾針。
不管是毫無尊嚴地活著還是意外兇險地死去,我們都是不能接受的。相比之下,安樂死能夠沒有痛苦、相對體面地結束這一切,成了一個極具吸引力的選擇。現在說起來像笑談,但當時我們四五個差不多年紀的病友,曾認認真真地研究過路線、流程以及如何聯系,想要組團去死。直到一個病友聯系了瑞士相關機構,被告知一個人的費用大概要 30 萬元人民幣。
“ 30 萬元?算了算了,別再給家里添負擔了。”至此大家就沒有再討論過這個話題。
死都這么貴,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
老朱從不參加“組團赴死小分隊”的討論,他說他是家里唯一的收入來源。“我死了就死了,但是能多撐兩天就多撐兩天,能多領幾個月工資,媳婦孩子就有飯吃。”
說這話的時候,我倆站在病房的窗戶前。樓下一個撿垃圾的流浪漢恰好經過,老朱打住話頭,盯著那個身影,眼里全是羨慕。想必我目光的成分跟他并無二致。那個流浪漢能四肢康健地沐浴著陽光,而且,似乎擁有綿延的生命。
而我們,已經進入了倒計時。
剩下的日子,
你要怎么過?
人真是一種復雜的動物。我一邊研究死,一邊海量地查文獻、看論文,想要找到活命的機會;一邊覺得自己已經接受現實,接受死亡,該工作工作,該開會開會,一邊又在夜里輾轉反側,盯著黑漆漆的屋頂發呆。
其實從第一次見樊東升醫生的那天開始,我就睡不著覺了。住院后,這種情況變得越發糟糕。
醫院晚上 10 點統一熄燈,我習慣性地在手機上繼續處理一些事情,仿佛只有在工作、鉆研文獻時才能暫時忘記自己的病人身份,一旦躺下,潛意識中的絕望和焦慮馬上就會奔涌而來。強迫自己閉上眼睛,卻感覺閉著眼比睜著眼時看到的東西還多、還雜。耳邊細微的嗡嗡聲讓一切顯得不真實,我分不清那個聲音來自耳朵還是大腦,是夢境還是現實,只覺得夜晚的安靜又將那個聲音放大了數倍。迷迷糊糊之間又突然完全清醒,點亮手機,2:06。左臂上的肌肉仍在持續地跳著,像是在用盡全力跟我做最后的告別。想想未來幾年里,全身上下的每一處肌肉都會相繼喪失功能,直至全部喪失。2 年?3 年?或者老天眷顧,能留給我 5 年?腦子里閃著這些數字,慢慢模糊,不知多久后又瞬間變清晰,一看時間, 3:20。為什么時間過得這么慢?不,為什么時間過得這么快,為什么不能多留給我一些時間,為什么是我……一連串的“為什么”“憑什么”“怎么辦”旋轉著涌入一個沒有盡頭的隧道,我被推搡著一直往前卻一直走不出去。等終于看到前方一個亮點,像是隧道出口,一睜眼,時間已經指向 5:00。護士要來抽血了。
有半年的時間,我每天夜里幾乎都是這種狀態,即便勉強睡著,一晚也要醒四五次。這種狀況在病友中極其普遍。絕癥患者一般都會伴有心理問題,在海嘯般的絕望、恐懼、焦慮面前,人會被瞬間吞噬。不少人會陷入抑郁,所以醫生會主動給開一些抗抑郁的藥。
我的藥也擺在床頭柜里。這類藥多少都會有些副作用,會讓人昏昏欲睡,那樣的話日常工作、開車都會受影響。我糾結了很久,最終還是一粒都沒吃。吃藥后昏沉的大腦和睡不著覺困倦的大腦,我寧愿選擇后者。既然我明確知道海嘯的源頭在哪里,那么與其在下游拼命地舀水,不如直接去根源解決問題。
我也同樣拒絕吃力如太。目前它是世界上唯一能夠延緩漸凍癥,能夠從死神手里搶下 2~3 個月存活期的“特效藥”。住院第 17 天,醫生給我開了一盒,讓我趕緊吃起來。
之前我雖然嘴上不說,但心里仍多多少少抱有希望,覺得自己可能并非漸凍癥。畢竟做了兩個多禮拜的檢查,醫生始終沒有寫下明確的診斷。而“力如太”的到來則無異于用另一種方式宣判了我的死刑。
如果真的是漸凍癥,多活兩三個月有意義嗎?
躺在床上睡不著,我就戴耳機聽李開復的《向死而生》。這是他在戰勝淋巴癌之后寫的書,與死神擦身而過,讓他開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在書中,他得出了一個樸素又近乎是真理的結論:健康、親情和愛要比成功、名利更重要。李開復從中獲得了對抗疾病的力量和勇氣。
反觀我自己:人生 41 載,我又獲得了什么呢?
用現在的流行詞來說,我就是典型的“小鎮做題家”,出身五六線城市,只能靠勤學苦讀走出小地方、走向大城市,改變人生命運。但對我來說,“苦”的不是讀書,苦仿佛是我人生的底色,我常形容自己是“苦大仇深”,堅信“一切都要靠自己打拼”。這也是父親從小灌輸給我們的理念。
父親是個軍人,農村家庭出身,兄弟姐妹七人,他是老大。家里最餓的時候連活老鼠都吃過。后來他成為一名軍人,也成了大家庭的頂梁柱。退伍后他轉業到商丘市財政局。在我們家,他把吃苦耐勞、堅韌不拔的軍人作風發揚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對我和哥哥極其嚴格,每次吃飯基本都是給我們上思想課,教育我們要好好學習,努力拼搏。
從小我就知道我家條件不好。我們住在一個部隊大院,不知道為什么,別人家都住著帶暖氣的樓房,而我家是平房,沒有暖氣不說,屋里還四面漏風,到了冬天室內都能結冰,手腳凍得紅腫潰爛。壁虎、蟲子在墻壁窟窿里爬來爬去。我和哥哥沒什么玩具,玩的都是別的孩子扔掉的,穿的也是打補丁的衣服。在這種條件下,要想過上好的生活,就要比別人做得更好,而我們也不聰明,只能笨鳥先飛,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
所以從五年級開始,我每天四五點起床,跑步、打拳、背英語。上了省重點中學,我經常是全班第一名,全校第二名,考試大部分功課都是 100 分,同學們都管我叫“外星人”。但其實大家并不知道,我經常強制自己用一半的考試時間就提前交卷,多數科目依然可以拿到滿分,以此嚴苛要求自己。
高考后,父親在我的志愿表上填報了中央財經大學。他自己做財務,所以認為我學財務也理所應當,但我極度抗拒。我的目標是北京大學,而且要上我最喜愛的空間物理學專業,因為我一直的夢想就是當科學家,探索宇宙,探索 UFO(不明飛行物)。
不過家里的現實條件沒給我反抗的機會。父母都是窮人出身,在他們眼里,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一項能夠傍身的技能養活自己,不是很好嗎?
最終我還是服從了他們的意愿,科學家夢想破滅,還因此抑郁了三年。現實也容不得我繼續抑郁,大三那年,年僅 47 歲的父親去世,不僅讓家里失去了頂梁柱,而且為了治病我們幾乎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積蓄。為此,趕緊畢業掙錢是我當時唯一的選擇。
兒時家庭生活的窘迫和時常面對的困難,鋪就了我人生的底色。大學畢業后,我進到機關單位工作,當公務員,后來又以全國統考系內前三名的成績考取了中央財經大學稅務系的公費研究生,師從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前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財經大學稅務系主任郝如玉教授。研二時,我被借用到國家稅務總局政策法規司稅改處,參與了企業所得稅“兩法合并”(當時我國實施《企業所得稅法》和《外商投資企業所得法》雙軌制)提案等工作。研究生畢業那年,我參加了國家部委公務員考試,考了 150 多分,超出錄取線幾十分,但最終我選擇了另一條道路,進入當時世界 500 強排名前十位的三星集團,在中國總部擔任稅務經理,由此開啟了我職業經理人的生涯。在那里,我接受的理念是“員工不加班,公司必然死亡”,員工就要為公司拼搏、拼搏、再拼搏。29 歲,我又加入萬科任集團總稅務師,那時候半夜離開辦公室是常態,周末、晚上都用來研究房地產行業。
2011 年年底,我加入京東,有幸參與支持京東上市相關工作。2013 年 6 月,我帶領團隊開出了中國內地第一張電子發票,每年可為公司節省上億元的財務成本,并將電子發票成功推廣到各行各業。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我幾乎都是利用夜晚和周末的時間連續創業,為公司開拓新的價值。
我發過一條朋友圈:“沒有誰強迫我加班,但我晚上總是工作到很晚,被人說是工作狂,可是我真的很有熱情,尤其是面對棘手復雜的問題,事情越棘手、越難搞、越有挑戰,我就越充滿激情,越覺得又是我發揮能力的好機會,工作干得越爽。”
時間都投入在工作上,生活自然是枯燥的。我就是一個枯燥的人。在 40 多年的人生中,我幾乎沒有專門外出旅游過,別說是出國旅游,連國內游都幾乎沒有。僅有的兩次出國,一次是 2013 年,為了拓展京東的國際化業務,去了俄羅斯;一次是 2015 年京東組織高管去美國硅谷考察。僅有的一次國內游是跟夫人去拍婚紗照。在北京上學和工作 20 多年來,我連故宮和長城都沒有參觀過。每年的年假也基本都是正常工作,連婚假都沒休。
我幾乎是在用別人雙倍的速度回答著人生這份考卷,正如十幾歲的我偷偷做的那樣,總試圖用一半的考試時間就交卷,且仍要求自己拿滿分。老天爺大概也掐著表,在我人生半程剛過就提前過來,想要把卷子收走。然而這一次我還沒答完,也不愿意離開考場。
我還能做點什么
這兩年很多媒體采訪我,經常會問我一個問題:“如果你知道會得這個病,之前 40 年還會選擇一心撲在工作上嗎?”
在他們看來,我就是一部工作機器,一個不能接受哪怕一分鐘不工作的“奇葩”。我也知道他們大概已經預設了答案,那就是“不會,我會用更多的時間來陪伴家人、享受生活”。這可能也是大多數絕癥患者的選擇。
但我的真實想法是:我仍然會像以前那樣做。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這個世界第一絕癥橫在我面前,把毫無防備的我推下深淵時,很大程度上正是那種已經成為慣性的要強和拼搏勁頭拽住了繩子的那一頭,把我從深淵中一點點拉了上來。住院期間,除了劉強東劉總等個別領導和我的少數下屬,公司上下都不知道我得病,因為我依舊參加各層級的會議,按時提交高管周報,手上的項目一個不落地向前推進。在一天天充滿煎熬的檢查和等待中,與其說工作需要我,不如說我更需要工作。
當然,繩子那頭拉住我的還有更多的東西。
一天晚上 11 點半,早過了病房的熄燈時間,我還在查資料、處理工作,一扭頭發現老朱還沒睡。平時這個點他早該休息了。
“你咋還不睡?”我問他。
“等你呢。”
我突然想到,之前閑聊時他問我怕打呼嚕嗎,我隨口說:“肯定怕,但是我先睡著的話你隨便打,多響我都不會醒來。”無意間的一句話,老朱竟然記到了心里,每天都是等我先躺下,他再睡。
這么好的人,為什么不能多活幾年?
住院之前,我接觸的基本都是商業精英或者工作上的合作伙伴,而這一個月來我結識了好多天南海北的病友,有些甚至不識字。以前我從未想到會和他們產生交集。他們都這么善良,本該擁有幸福的人生。
我想幫助他們。
這么多年來,我一直要求自己成為一個強者,甚至成為王者,一次次努力超越別人,這也是社會的主流追求。但靜下心來想,其實我們已經很強了,強大到具備了幫助別人的能力。相比于這些病友,起碼現在我的身體狀況要強不少,我還能正常行動,還有兩三年時間可以支配。而且坦誠地說,在調動社會資源方面,我也更有優勢。
這大概就是上天要交給我的使命,它仿佛在說:蔡磊,這個病很殘酷,所有病人都無比絕望,你還有點兒能力,愿不愿意為這個病的救治做點什么?
毫無疑問,我愿意。
我不是沒想過趁有限的時間去旅游、享受生活,但我心里知道,那不是我,也不是我想要的。我的病友要么已行動不便,要么只能臥床維持,但是我還能戰斗,那我就該去戰斗。如果我們
自己都不努力,還能奢望別人為我們努力嗎?
從敏捷戰略到高效執行
OKR目標管理法 實踐落地工作坊
關鍵詞:
-
觀察:通用技術中國醫藥三款產品中標第八批全國集采
資訊 23-03-31
-
火炬之光2存檔位置在哪?火炬之光2共享倉庫怎么用?
娛樂 23-03-31
-
大理寺發展都經歷了哪些階段?大理寺的官職設立和職責是什么?
社會 23-03-31
-
全球微動態丨徽州區:用好用足稅收優惠 激活徽州高質量發展“一池春水”
資訊 23-03-31
-
帝王權術是什么?帝王權術的特征是什么?
教育 23-03-31
-
止損線如何設置? 止損線一般為多少合適?
資訊 23-03-31
-
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分別是什么意思?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兩者有什么區別?
金融 23-03-31
-
羅伯遜:仍相信我們能在各項賽事競爭,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得進前四-世界熱資訊
資訊 23-03-31
-
星際爭霸2配置有什么要求?星際爭霸2是個什么游戲?
服務器 23-03-31
-
什么是安防監控?安防工程包括哪些項目?
安全 23-03-31
-
雙系統如何引導修復?雙系統引導修復工具詳細操作流程是什么樣的?
服務器 23-03-31
-
三國塔防魏傳怎么修改?三國塔防魏傳為什么下架?
智能 23-03-31
-
三星r428筆記本參數是多少?三星r428快捷鍵驅動安裝方法及常見問題有哪些?
智能 23-03-31
-
4月用戶側電價分析:超6成區域峰谷價差同比增長 新視野
資訊 23-03-31
-
dota巨牙海民如何出裝?dota中哪個職業克制惡魔巫師?
大數據 23-03-31
-
魔獸世界獵人稀有寵物都有哪些?魔獸世界獵人天賦怎么點?
互聯 23-03-31
-
從“高考狀元”到貪腐兩千多萬被查:四川簡陽原市長易恩弟懺悔書披露 環球微資訊
資訊 23-03-31
-
省消保委提起全國首例醫美領域消費民事公益訴訟 天天快看點
資訊 23-03-31
-
即時:送老舅的生日禮物
資訊 23-03-31
-
王博:諸暨對CBA的幫助是非常巨大的 由衷地感謝你們 環球新動態
資訊 23-03-31

閱讀排行
- 一個 45 歲的男人決定“打光最后一顆子彈”_天天亮點
- 【天天速看料】和訊個股快報:2023年03月31日 豆神教育(300010)該股換手率大于8%
- BM11-C3-200KG-3B (BM11傳感器) ZEMIC 中航電測稱重傳感器 天天微資訊
- 網絡設備有哪些?網絡設備分為哪幾種類型?
- 天衣無縫劇情人物解析_天衣無縫劇情
- 鐵礦石價格異動不可掉以輕心
- 廣晟有色:2022年凈利2.32億元 同比增67.03% 世界熱頭條
- 珠光控股(01176.HK)發布截至2022年12月31日止年度業績,該集團取得收入28.39億港元,同比下降4.9%
- 國內首臺超大直徑TBM/泥水雙模式隧道掘進機“華隧奮進號”正式下線
- 啟動改造!涉及六安城區11個小區!
- 環球訊息:布依族圖騰
- 蒜蓉炒油菜的做法_蒜蓉小油菜
- 貴陽五中怎么樣_貴陽五中 環球速讀
- 三星schi509怎么強制恢復出廠設置_三星sch i509
- 榮耀平板5玩和平精英(榮耀平板5怎么樣) 世界新動態
- 姚曼:我是蔣大為情人,他欠我90萬,有欠條為證,蔣大為:都是她逼我的
-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主體和客體的關系_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物質是
- 就在今天,威少成為歷史第一:在5支球隊砍下至少30分10助攻!-焦點報道
- 今日訊!柯林斯宇航再獲中國商飛年度優秀供應商兩項大獎
- 每日消息!走吧,去濟寧 | 刀槍劍戟 鋒芒畢現
精彩推送
- 迅雷云盤在哪打開?迅雷X怎么設置下
- 好柿花生app挑戰金可以退款嗎?好柿
- mate50pro怎么開省電?mate50pro怎
- iphone14支持5g網絡嗎?iPhone14系
- 原神劫波蓮位置采集路線分享?原神
- redmipad省電模式在哪里開?redmipa
- 右鍵菜單上傳到迅雷云盤選項怎么刪
- 網易有道詞典怎么設置年級信息?網
- vivo即將發布操作系統OriginOS3 新
- 163郵箱怎么登錄?163郵箱怎么撤回郵件?
- crm系統怎么改密碼?crm系統數據如
- 密室逃脫6圓盤怎么轉?密室逃脫6如
- 語玩怎么將我的動態設置為隱私動態?
- 黑盒工坊版本更新日志如何查看?黑
- 小影app怎么取消自動續費?小影怎么
- 安卓優化大師怎么卸載?安卓優化大
- 夸克瀏覽器神秘入口關鍵詞大全?夸
- 掌上新華app保單貸款怎么辦理?掌上
- 瀟湘高考怎么看錄取狀態?瀟湘高考
- 怎樣看神馬影院?神馬影院播放時資源